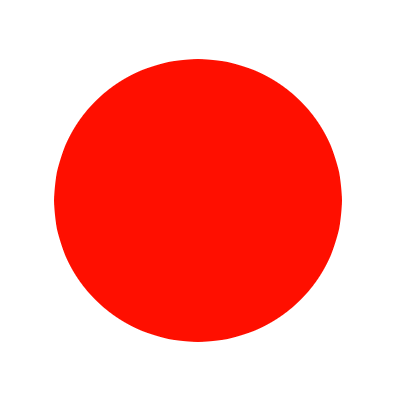牧羊人讀書筆記 (朱敬一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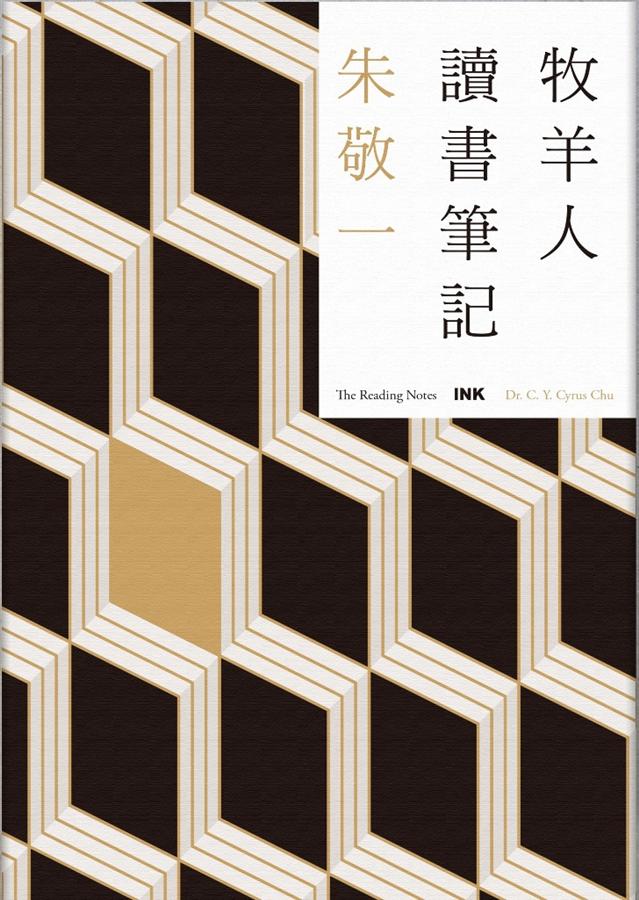
-
我們這一代親身參與了數位時代的建構,下一代卻容易形塑成「生於深宮之中,長於谷歌之手」的知識與智慧的失落的一代。 (p.11)
-
一旦某人想要 master the rules,我認為十之八九他已經沒有改變規則的野性與衝動。想要孰悉規則的人,通常再也難以改變規則。 (p.19)
-
讀書不是為了「有用」而讀,至少事前不知道有什麼用;但是我們越是不執著於其應用,就越能自然而然地找到應用的方向。幾十年來這是我一貫的看法,名之為「不住相讀書」。不住相讀書,就自然而然能夠孕育涵養。 (p.21)
-
拼命閱讀「如何寫作文」,反而對作文沒有幫助。 (p.29)
-
《金剛經》說:「菩薩不住相布施,其福德不可思量」;牧羊人說:「外交官不住相讀書,其功效不可思量」。 (p.29)
-
在我們旁觀者眼中,這些文字交鋒就像是武打片中「一方餵罩門給另一方打」一樣,消暑解渴。 (p.36)
-
「書法」所築基的繁體中文,是台灣與中國的重要文化分野之一。簡體字因為濃縮了文字架構,當然也就妥協了書法藝術。 (p.38)
-
搜尋引擎也許可以節省余先生的時間,但是卻完全無助於人文知識的累績與成長。 (p.41)
-
電影《一代宗師》有句對白:功夫,兩個字;一橫一直。我認為「人文學者」也就只有兩個字:或通或滯。余公之後,我找不到庶幾乎近的通儒型漢學研究者。要彌補這個空檔,絕對不是獎勵問題,而是教育問題。 (p.42)
-
基本上,要成為大學者,都要有頗長一段時間「極為專注」地投入研究。那種專注,幾乎是到了完全不旁騖其他的地步。 (p.46)
-
數學大師也不是一開始就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」,還是要摸索、嘗試、犯錯、修正。 (p.47)
-
如所周知,所有一門深入的專注,都不利於因應環境劇變。遍地開花的龐雜,卻往往恰能找到環境改善下的因應之道。 (p.52)
-
功夫,是在「合乎物理原則」的前提之下,做出凌厲的攻擊或是靈巧的防禦動作。 (p.57)
-
任何一個功夫門派的所謂大師,想靠格鬥獲勝而取得某種正當性,我認為都已經誤解了「功夫」的意涵,已然不足論矣。 (p.65)
-
我對於好餐廳的定義非常簡單:自己願意花時間、花錢去吃飯的地方。 (p.67)
-
我當然不是豪門巨富,「花錢」吃飯是會痛的。如果再加上時間,那麼要求的回報當然更高一些。 (p.67)
-
牛排熟成靠冰箱溫控,火候靠烤箱時間控制,全是電子控制的機器。烹調至此,不是科技業嗎? (p.68)
-
現在完全著重肉質沾海鹽的吃法,像是舊石器時代的品味;真抱歉,我不太願意「付錢去體驗舊石器時代」。 (p.68)
-
坊間又興起另一個歪風:所謂創意料理。我們這種做研究的人最清楚:天底下哪有那麼多創意?於是,上主菜端上臉盆大個盤子,上面一小片杯口直徑的肉,上緣配一根乾癟樹枝,盤子上撒上幾滴由小漸大的、嚐之像是油膏的黑點。這是創意?也許我台大待久了,直覺上這是「研究創新造假」!這種西餐,我不願意「付錢配合造假」。 (p.69)
-
有些歌,大概某人唱過之後,別的歌手就不敢唱了,因為「自嘆不如也」。 (p.69)
-
從這個角度來看,生物的演化過程真的很像經濟學的分析。 (p.77)
-
今天存在的物種,都是「在追求淨繁殖率極大,但是長期淨繁殖率是零的」。這與完全競爭均衡所描述的「廠商追求利潤極大,但均衡利潤為零」,不是很像嗎? (p.77)
-
大部分的「智慧」,都是動物在年幼時期培養出來的。所以年幼期間長,是該動物長大時能夠擁有高智慧的關鍵。 (p.79)
-
停經的母性生物從天擇的角度來看「根本沒有存活的價值」,所以生物界不應該出現停經這種現象。 (p.80)
-
「停經」的祖父母仍有繁衍的價值,因此停經並不會在演化中被淘汰。 (p.80)
-
演化生物學鼻祖漢米爾頓早在四十年前就指出:「生物的死亡率應隨其剩餘繁殖力之下降而上升。」這就是一般所謂「老化」。 (p.81)
-
如果人類的幼年期有十五年,十五歲起開始有繁殖能力,則對父母而言,最浪費的死亡模式是「十五歲死亡」,而最節省的死亡模式是「新生兒死亡」。 (p.83)
-
當代演化生物學的共識是:要解釋公孔雀的大尾巴,必須要仰賴「訊息不對稱」的均衡理論。 (p.85)
-
在演化過程中,一個能夠讓強壯孔雀凸顯其真正強壯的辦法,就是「呈現弱點」。 (p.86)
-
我的笑話是譏諷性的,但是在開放的笑容與餐敘的禮儀包裝下,看起來純粹是玩笑。 (p.90)
-
通識教育大師哈金斯 (Robert Hutchins) 曾經說,通識教育的核心概念,就是延伸貫穿;貫穿時間、貫穿地域、貫穿科學。 (p.93)
-
我認為,學術研究是一個極盡馳騁、絞盡腦汁的「過程」。有的人可能研究出重要結果,有的人只能寫餖飣雜文。做研究不該有什麼極簡主義;最後的研究結果若流於淺窄,是研究者不得不消極接受的結果,怎麼說也不該成為積極的主義。主義是「一種思想、一種信仰、一種力量」;餖飣雜文、一鱗片爪的芝麻結論,憑什麼成為思想、信仰、力量? (p.94)
-
有時候在學術界,你得創造一些炫酷的名詞,諸如「父權自由主義」。即使這個名詞邏輯不通,它只要音韻合拍、容易引起討論,就有搧風點火的功能。創造名詞的人因此成就了一家之言,其他的考量,就不關他們的事了。 (p.95)
-
一般而言,歹事歹念經常源於當事人的相對挫折,或是難以在既存制度下出頭的「積怨」,只好透過某種偷搶拐騙的手段,去達成某些壓抑在心底的目標。 (p.104)
-
畢竟,「魯蛇」二字,絕對只是同輩比較的結論,與數百年來歷史有什麼變化,完全沒有干係。 (p.105)
-
特權研究的問題是:別人沒有辦法重複,或是很難複製,以驗證或是反駁這兩位學者的研究結果。兩位學者也許沒有壟斷資料,但別人真的很難有機會駁斥其結論。科學哲學家波普爾 (Karl Popper) 說,科學就是提出「可被檢證或棄卻的假說」。B&D 這樣的研究,是否能符合科學的要求呢? (p.117)
-
該雜誌評論文章最後提到:「經濟學家根本解決不了貧窮問題;也正因為他們解不了貧窮問題,所以他們才有那麼多『貧窮研究』可以做!」 (p.118)
-
古人說,一人得道,雞犬升天。照《經濟學人》的批評,反而是一人得獎,經濟學界卻被看扁了。我想 B&D 得獎的真正傷害,正在於此。 (p.118)
- 遺產贈與稅的理論基礎改有以下三種: (p.121)
- 保險機制:遺贈稅像是子女世代立足點的資源重分配,是子女輩在「不知道自己將生於何種家庭」情況下的一種「保險」機制。所謂「不知道自己將生於何種家庭」,是羅爾斯 (John Rawls) 「無知之幕」的觀念,在這裡非常適用。
- 矯正資源配置:家庭財富與子女能力通常相關性不高,故我們常見富二代無效率地揮霍,而窮二代卻有能力者徒呼負負。
- 合乎動態公平:哲學家德沃金 (Ronald Dworkin) 指出,動態公平的社會應該是「多回饋努力、少獎勵機運」。
-
網路上一則笑話:富二代經常被人誤認為孤兒,因為他們動輒問別人,「你知道我爸媽是誰嗎?」 (p.122)
-
坊間有所謂「遺贈稅率調降到百分之十,才能收到較多稅收」,以此去合理化百分之十的稅率。 (p.123)
-
看看二○一九年的香港「反送中」衝擊,台灣能夠沒有國防嗎?台灣適合與香港比嗎?台灣政府對企業的服務,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國家,應該是十七%的稅率所不足因應的,故有調高之議。 (p.133)
-
為了內外資稅差區扭曲綜合所得稅的平等原則、累進原則,是捨本逐末,卻大大圖利了股利所得占比高的大富豪。 (p.137)
-
「為理念,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 (p.139)
-
有錢家戶的致富來源是土地與股票,而不是靠工作賺來的薪水。 (p.143)
-
過去二十年,台灣的所得不均跟財富不均都在惡化中,也驗證了「富者越富」的趨勢。財產多、賺得金額多,沒關係;但是財產多、「報酬率」高,就有關係。造成「不公平」最大的關鍵,還是報酬率跟租稅政策。 (p.148)
-
民族主義者強調兩岸人民文化同源、種族同根,不允許同族同胞自外於中國。而拒絕「一中原則」的九二共識,就是「自外」的開始,當然不能接受。 (p.172)
-
媒體分析,卡麥隆首相的表態在憲政體制之下不但沒有意義,甚至也許還有反效果。 (p.173)
-
民主不只是「我們這一代」人的決策要循一定的程序,民主必須是指「每一代」人民實踐憲政程序的意志不受扭曲、不被壟斷。如果老祖宗的決定可以約束我們這一代的決定,說我們「不能做這個、不准選那個」,那麼我們現在就沒有真正的民主。 (p.174)
-
舉例而言,「終極統一」或「終極XX」的論述,就限縮了未來子孫「不要統一」或「不要XX」的民主選項。這樣限縮未來世代民主選擇的訴求,不符合永續民主的理念,也就不是真正的民主。 (p.176)
-
習近平主席所定位的一中各表示「兩岸同屬一中,謀求國家統一」,這顯然是限縮未來子孫的選項。 (p.177)
-
兩岸之間的根本差距在於「民主」,而不是「民族」。 (p.178)
-
政經學者何泰凌 (Harold Hotelling) 與唐斯 (Anthony Downs) 在半個世紀前就指出,普選的關鍵字就是「中位數」。 (p.183)
-
拔尖是追求極值,中位數是呈現平庸,用普選去選出拔尖領導人,這是邏輯矛盾、緣木求魚。 (p.184)
-
普選或是任何曝光候選人的假遴選,德高望重的清流之士都會望而卻步,這就是反向選擇。 (p.186)
-
就資安而言,我比較接受「理性主義」。通常,我們經過暗巷,看到兩旁遊手好閒的兄弟覬覦的眼神,就足以判斷「那個暗巷不太安全,要避免經過」。大概沒有哪個白癡要「親身經歷一次搶劫,被狠揍一頓」,才能判斷暗巷安全與否。 (p.197)
-
一九八○年代北京流行這樣一個笑話:某個丁字路口,向右路標指通往資本主義,向左指通往社會主義。柯林頓到了路口,毫不猶豫右轉; 葉爾欽到了路口,考慮了一下,還是向右轉;鄧小平南巡也經此路口,他下車把路標對調方向,然後右轉。 (p.203)
-
整體而言,俄羅斯的貧富不均遠比中國嚴重,這也是《世界不平等報告》一書呈現的結果。 (p.207)
-
小鄧當年「摸著石頭過河」的方案,後來就逐漸成為中國的「試點」。 (p.208)
-
也許更根本的問題是:極權國家的集體主義,其國家的「目的」究竟是什麼?是誰來決定這個目的?所謂摸著石頭「過河」,河的對岸是什麼?如果集體主義在邏輯上就定義不出對岸,那麼怎麼過河,又有什麼差別呢? (p.209)
-
《金剛經》一段話!「汝等比丘,知我說法,如筏喻者,法尚應捨,何況非法。」 (p.210)
-
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沈恩 (Amartya Sen) 在其著作《正義的理念》中說,只有極權國家才會有大規模的饑荒。原因是:糧食其實是能引進的、夠賑災的;只是極權體制的種種僵硬,使得糧食偏偏就是到不了飢民手上,而且此種體制僵硬無從修正,所以才會產生饑荒。 (p.212)
-
這種「家境富裕、精神失常、不肯服藥、暴力傾向」的僵硬症候群,才是柯林頓把中國引進 WTO 的關鍵錯誤。 (p.213)
-
對中國而言,經濟成長只是麻痺人民、令他們在舒適生活下不致反抗的鴉片。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有毛澤東所寫「為人民服務」五個字。但那是狂犬病患者的深夜囈語,與極權統治的現實差距十萬八千里。 (p.214)
-
報酬遞增就表示「現在占優勢的,未來就更容易占優勢」。 (p.235)
-
老美討厭老共高姿態作弊,居然還冠冕堂皇喊出個「中國製造二○二五」的口號,但是又沒有辦法依現有 WTO 規則提起控訴,所以就說:「你作弊就作吧,但是不管你作弊完之後生產出來任何東西,我都把你課稅課到痛。」川普政策的白話文,就是這樣。 (p.237)
-
只有在單一問題面向,才有所謂「選邊」;或東或西、或戰或和之類。但若問題面向有七、八個,「選邊」就是個不當簡化的概念。 (p.240)
-
我們不能只要求交往,而不談交往的「條件」。 (p.245)
-
美國:「老弟,我忙著在對付反恐與中東,希望你不要在東亞給我惹麻煩」;中國:「老大,只要台灣別刺激我,我就不會招惹你」。 (p.248)
-
在這樣的默契下,老美定下「秩序」要台灣依循,而這個大秩序之下,台灣可以適度折衝,甚至左右逢源,做到「尾巴搖狗」的地步。 (p.248)
-
二○一○年有「阿拉伯之春」事件:不識彼此的阿拉伯民眾透過手訊息呼朋引伴,成功串連,發動了幾十萬人的大規模群眾運動,居然就把獨裁政權推翻了。 (p.257)
-
「六月四日」敏感,於是有人發明了「五月卅五日」作為暗語,結果沒有多久也就被網軍發現、查禁。 (p.258)
-
勞工與資本家之間的矛盾,是一個「分配」問題,不是一個效率問題。 (p.278)
-
提升效率與改善公平是兩個平行議題。當台灣官員說簽某個協定「利大於弊」時,其實根本沒有回答受損抗爭者的問題。提升效率的定義就是指整體利大於弊,而這背後就必然有人受損有人獲利。 (p.279)
-
自由競爭的市場雖然卻能提升效率,但是國際貿易市場卻從來就不是自由競爭市場。 (p.279)
- 在資本主義興起的兩百多年時間裡,勞工往往是被資本家壓迫的對象。資本可以跨國移動、資本家可以與政府高官眉來眼去、資本家對勞工條件有壟斷能力,但勞工卻完全沒有資本家的這些條件。 (p.280)